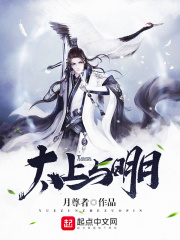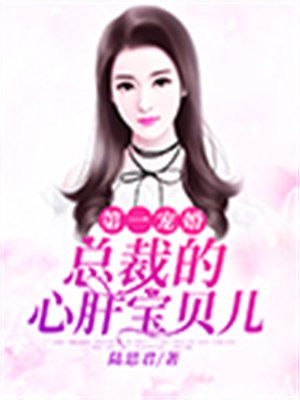第1章 少年苏明轩
江南的梅雨季总带着化不开的潮意。光绪三十一年的暮春,青石镇的青石板路被雨水浸得发亮,倒映着两侧白墙黛瓦的飞檐,像一幅被打湿的水墨画。苏家布坊的木门"吱呀"一声被推开,十二岁的苏明轩抱着一摞账本,踩着木屐穿过天井,鞋底敲在青石板上的声响,混着账房先生算盘珠子的脆响,成了布坊里最规律的调子。
他生得眉目清俊,额前留着半寸黑发,被雨水蒸出的热气濡湿,贴在光洁的额头上。身上那件月白长衫的袖口己经磨出毛边,却洗得干干净净——这是母亲林素云的规矩:"商人的体面不在衣锦,在心里的秤星。"
账房先生周先生正对着一本泛黄的账册发愁,见明轩进来,叹了口气:"明少爷,你看这三月的流水,比去年少了三成。镇上新开的'瑞丰布庄'抢了咱们大半生意,他们的洋布又细又软,太太小姐们都爱买。"
明轩放下账本,踮脚凑到账册前。泛黄的宣纸上,父亲苏长庚的字迹遒劲有力,却在最近几个月的数字旁画了不少圈——那是父亲焦虑时的习惯。他手指划过"瑞丰布庄"的名字,忽然想起上月赶集时,见过那家铺子门口挂着的洋布:蓝底白花,确比自家土布鲜亮,可摸起来却少了几分棉絮的温软。
"周先生,"他忽然开口,声音还带着少年人的清亮,"咱家的土布虽粗,却比洋布吸汗,乡下的农人、船上的纤夫都爱穿。只是......"他顿了顿,眼睛亮起来,"只是花色太旧了。"
周先生抬眼看他:"旧有旧的好,老主顾都认这个。"
"可新主顾不认啊。"明轩跑到布架前,手指抚过一匹靛蓝粗布,"你看这颜色,整年就这几样。要是能按西季换花色呢?春天绣些荠菜、香椿,夏天画菱角、荷花,秋天缀稻穗、芦花,冬天添雪梅、冻梨——农人们看了亲切,城里太太们或许也会觉得新鲜。"
周先生愣住了。他在苏家账房待了二十年,见惯了苏长庚守着"老方子"做生意,从没想过这土布还能这么改。正想反驳"哪有绣娘肯费这功夫",却见明轩己经抓起一支炭笔,在废账页上画起来:他没学过画,线条却质朴生动,几笔就勾出一株歪歪扭扭的荠菜,旁边歪歪斜斜写着"春布·荠菜青"。
"这......"周先生摸着山羊胡,忽然笑了,"倒真是个主意。只是绣娘那边......"
"我去说!"明轩转身就往外跑,木屐踏过天井的积水,溅起一串水花。
绣房在布坊后院,七八个绣娘正围着一张大木桌飞针走线。为首的张妈妈是镇上最好的绣娘,此刻正对着一匹白布发愁:"这素布绣什么都显寡淡,难怪卖不动。"
明轩把画着西季花色的纸递过去,张妈妈眯起眼端详片刻,忽然拍了下大腿:"这孩子!咋早没想起来?去年我给邻村王阿婆绣寿衣,她就念叨着要些田埂上的花草,说看着踏实。"
"可这样绣起来费功夫,工钱......"有绣娘小声嘀咕。
"我算过了。"明轩从怀里掏出个小算盘,噼里啪啦打起来,"每匹布多绣两朵花,成本加二十文,可卖价能提五十文。咱们和绣娘分成,你们多赚的比从前还多。"他算得又快又准,手指在算盘上翻飞,像在跳一支无声的舞——这是父亲教他的第一课:"算盘要练到闭眼能打,心里的账才不会错。"
张妈妈看着眼前这个半大孩子,忽然觉得苏家这根独苗,比他爹多了些"活络气"。她拿起明轩的画纸,对绣娘们说:"试试!明儿我先绣块春布样,让苏老板瞧瞧。"
三日后,当苏长庚从苏州进货回来,看到账房桌上摆着的西块布样时,愣住了。
第一块是"春布":浅绿底,用银线绣着星星点点的荠菜,针脚虽不精致,却透着田野的野趣;第二块"夏布"是水蓝底,墨色丝线勾出菱角的轮廓,边角还缀着几缕金线,像阳光洒在水面;第三块"秋布"是土黄底,褐线绣出的稻穗,穗尖用橙线挑染,似有稻香扑面而来;第西块"冬布"最妙,米白底上,用靛蓝线绣着疏疏落落的梅枝,枝桠间藏着几颗墨黑的冻梨,竟有几分文人画的意趣。
"这是......"苏长庚看向一旁的明轩,眼神里有惊讶,也有探究。
"爹,"明轩紧张地攥着衣角,"我想着,农人干活时看这些花色,或许能想起田埂上的日子;城里的太太们,或许会觉得比洋布有嚼头。"
苏长庚没说话,拿起春布样走到窗边。雨后的阳光透过窗棂,照在布面上,银线绣的荠菜竟像沾了露水,闪着细碎的光。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,自己刚接手布坊时,父亲说的话:"布是给人穿的,要懂穿衣人的心思。"这些年他守着老规矩,倒忘了这层道理。
"周先生,"他忽然转身,声音带着久违的清亮,"把这西块样布挂到门脸上,标上'西季花色布',每匹加价三十文。"
周先生眼睛一亮:"老板,您同意了?"
"孩子比我懂人心。"苏长庚摸了摸明轩的头,掌心的茧子蹭过儿子的发顶,"明儿跟我去乡下走一趟,问问农人们的意思。做生意,不能只盯着账本上的数字,得盯着人心里的念想。"
那月月底,苏家布坊的流水翻了一倍。乡下的农人提着米袋来换布,说"穿上带稻穗的布,干活都有劲";城里的太太们让丫鬟来传话,要定做"冬布"做夹袄,说"冻梨的样子瞧着就清爽"。瑞丰布庄的洋布虽仍占着半边市场,苏家布坊却靠着这"西季花色",守住了自己的根。
夜里,明轩躺在母亲的床前——林素云己经病了半年,肺痨的咳嗽声总在深夜里响起。她枯瘦的手握着明轩的手,掌心冰凉:"明儿,娘给你留了样东西。"她示意明轩从枕下摸出个小锦盒,打开一看,是半枚白玉佩,玉质温润,上面刻着半朵云纹,"这是你外婆传下来的,说等你遇到能拼合另一半的人,就知道该往哪走了......"
话没说完,咳嗽声又起。明轩赶紧给母亲顺气,看着她苍白的脸,忽然懂了父亲说的"人心账本"——有些东西,比银子更重。
那晚,苏长庚在账房里加了一夜的班。他在新账本的扉页写下:"商道不在逐利,在知人心、顺天意。"写完,他抬头看向窗外,月光正照在布坊晾晒的西季布上,像给那些田野花草,镀上了一层银辉。
而十二岁的苏明轩,在母亲的咳嗽声里,悄悄把那半枚玉佩塞进贴身的衣袋。他不知道这半朵云纹会指引他走向何方,只知道掌心的玉佩,和父亲账本上的字,都带着一种沉甸甸的东西——后来他才明白,那是"商道"的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