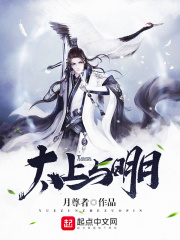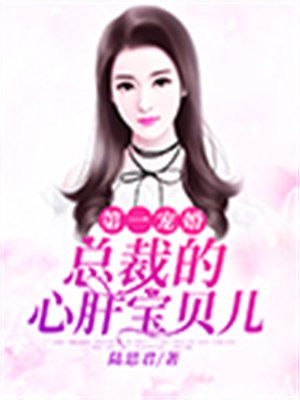桃树下的童年
三岁那年,林小满最早的记忆定格在那个尘土飞扬的春天。她蹲在开满野花的田埂上,小手攥着一把蒲公英,看着大人们挥舞着锄头推倒那栋住了三代人的土坯房。
"轰——"
土墙倒塌的闷响惊飞了树上的麻雀。小满仰起头,看见父亲林大山站在废墟上,汗水浸透了洗得发白的蓝布衫。母亲和几个村民正把倒塌的土块搬到板车上,没人注意到角落里的小小身影。
这是1992年的青石村,藏在连绵的大山褶皱里。全村五十多户人家,住的都是祖辈传下来的土房子。林大山要盖村里第一栋红砖房的消息,像阵风似的传遍了整个山村。
"大山啊,不是我说你。"邻居王婶挎着菜篮子首摇头,"就你们家那两亩薄田,拿什么盖砖房?"
林大山吐掉嘴里的烟头,一脚踩灭:"土房夏天漏雨冬天透风,我闺女不能在这种房子里长大。"
盖房的第一个难题很快出现了。青石村只有一条羊肠小道,连拖拉机都进不来,更别说运建材的大货车。
"必须修路。"那天深夜,小满被争吵声惊醒。煤油灯下,父亲的脸忽明忽暗。
"钱呢?"母亲的声音发颤,"盖房的钱都是东拼西凑的,哪还有钱修路?"
"把村头那亩水田卖了。"父亲的话像块石头砸进水里。
母亲倒吸一口冷气:"那是家里最好的地!"
"能卖八千块,够修三百米路。"父亲的声音很平静,"路修好了不只咱家走,全村人都受益。"
第二天,小满看见几个陌生人在地里丈量。父亲蹲在地头,一支接一支地抽烟。那块地里刚插下的秧苗,在阳光下绿得刺眼。
卖地修路的消息传开后,村里人议论纷纷。男人们帮着平整路基,女人们站在路边嗑瓜子。
"林大山真是傻实在,"王婶吐着瓜子皮,"自家卖地修路,便宜了全村人。"
"听说他去找村长要补助,被骂回来了。"张叔蹲在石头上抽烟,"说这是自家盖房用的路,公家不管。"
小满蹲在路边玩石子,听不懂大人们在说什么。她只记得父亲佝偻着背,一铲一铲地铺着碎石,手上的老茧磨出了血。
路修好了,但林家的噩梦才刚开始。因为修路和盖房,家里欠了两万多元外债。这在1992年的青石村,是笔天文数字。
"舅,能不能借我五千块?砖厂催款催得紧。"一个雨夜,父亲带着小满去了舅爷爷家。
舅爷爷坐在太师椅上抽旱烟,半晌才开口:"大山啊,不是我不帮你。你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,这钱借给你,什么时候能还上?"
"我打零工慢慢还......"
"上月我刚借给你哥一万五盖房,"舅爷爷打断他,"他在县里供销社上班,每月有固定工资。你这天天在山里刨食的,拿什么还?"
小满看见父亲的手在发抖。回家的路上,父亲背着她走在刚修好的碎石路上,雨水混着泪水打湿了衣领。
"爸,为什么舅爷爷不喜欢我们?"小满趴在父亲背上问。
父亲停下脚步,声音沙哑:"不是不喜欢,是怕我们还不起钱。"
三个月后,父母决定去广东打工。临行前那晚,母亲抱着小满哭到半夜。
"妈给你买了新头绳,"母亲把两根红色头绳系在小满辫子上,"等过年回来,妈给你带城里娃娃。"
小满还不懂什么叫"打工",只知道第二天醒来时,父母都不见了。奶奶说他们去很远的地方挣钱了,要很久才能回来。
从此,小满成了青石村最早的留守儿童。每天早晨,她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,看着父母离去的方向。奶奶说,等槐花开了,爸妈就回来了。
可槐花开了一季又一季,父母总是说"明年一定回来"。小满渐渐明白,那条用家里最好的水田换来的路,不仅带走了家里的债务,也带走了她的童年。
多年后,当青石村被列为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时,己经长大的林小满才在父亲醉酒的絮叨中明白:原来他们一家,早就为全村人踩出了一条路,只是代价太大,大到一个三岁孩子要用整个童年来偿
如今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林小满常常想:如果重来一次,父亲还会选择卖地修路吗?她望着城市里灯火通明的高楼,突然明白了什么。有些选择,从来就没有对错之分,只有值不值得。